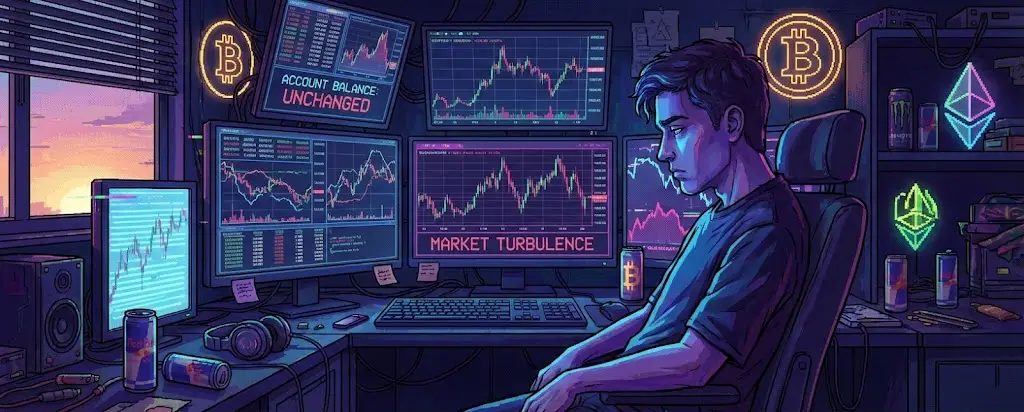月亮就这么烂掉了。
开始是几个小斑点,看着像发霉。没人当回事,都以为是大气层有灰,或者是宇航局实验又搞砸了。

到了第七天夜里,月亮上裂开一条黑缝,跟个眼珠子似的,慢慢张开,把光都吃了进去。
电视台的专家讲了一堆,给那个黑孔起了几十个名字,像什么“月蚀残斑”“深空影带”,后来信号全断了。
所有电视屏幕上都是一个画面,黑孔里有些纹路,看着像是一堆指纹,又像一堆人脸。
看久了的人,都开始做同一个梦。
关于伶听这个名字
我叫伶听,听我妈说,名字是旧纸里翻出来的,是古时候给守夜祭司起的名字。
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小城,靠老矿和旅游活着。河边的石壁上有些凹痕,有人说是古代文字,也有人说是矿车蹭的。
上小学的时候,校门口有块石碑,上面的字都看不清了,只有头几个字还能认出来:“天不再蓝之日”。
老师说,「这是上个世纪的环保口号,别在意。」
但我每次放学,都用手去摸那几个字,心里空空的。总觉得碑上原来还刻着很多东西,被人给抹了。
我十二岁那年,第一次做了那个梦。
梦里是灰的,一群人跪在干裂的河床上,对着一个黑塔。塔的表面不是石头,是一层层的皮,皮下面有东西在动。
塔顶站着一个“形状”,看不清脸。一想看清楚,耳朵里就有一堆声音,念叨着“尘母”、“灰君”、“夺昼者”这些怪名字。
最后这些声音合成一个,不男不女的,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。
它叫我的名字。
我吓醒了,手心都是血,被自己指甲掐的。去窗边看,月亮好好的。
第二天我把这梦跟我妈说了。
她听完,过了好久才说,「别再说梦的事。在这地方,梦会被听见的。」
我问,「被谁?」
她说,「被那些还没被写出来的神。」
月亮上开始掉东西
后来灾难就多了,冰川塌了,海平面涨了,城市年年发大水。
新闻上都是些“最后通牒”、“临界点”的词,人也都听麻木了。
所以月亮开始烂的时候,大部分人就是拍个照发网上,配句话说,「天有点怪哈哈。」
第五个月,黑孔把半个月亮都吃了。有个港口城市的人看见,月亮底下掉下来一条黑丝,跟蜘蛛丝似的。
黑丝一碰到海,海水一下就开了,几百公里内的海,几十秒就从蓝色变成了沥青一样的黑色。浪也不反光了。
然后就是鱼。
成群的鱼浮上来,身上没鳞片,眼睛是空的,嘴一张一合。设备录下来,是一种很低频率的震动。
科学家把这声音弄成图像,发现频谱图上的纹路,跟古时候石碑上的刻痕很像。
从那天晚上开始,全世界都有人开始梦见那座黑塔。
城里来的司机
我们这小城不靠海,灾难先是从消息传过来的。
网络时好时坏,电视上除了雪花点,就是专家出来让大家别慌。
街上人越来越少,学校停课,我爸的矿也停工了。我妈的餐馆里都是外地人,掏出现金放桌上,一边喘气一边说海啸、军队封锁什么的。
一个戴旧军帽的司机说,「那不是海啸。那玩意儿……往岸上爬。」
他说自己在路上,看见黑色的海浪里有东西的轮廓,不是鱼也不是船。像一堆人叠在一起,又像倒过来的树。
他说,「那些是从月亮里掉下来的。海只是个盆。」
我看到他的手抖得很厉害。
那天晚上,我又梦见黑塔。
塔更近了,跪着的人也更多。每个人的背上都长了一层干壳。塔顶上那个“形状”,我这次看清楚了,那是一堆“名字”缠在一起成的结。
都是些被忘掉的称呼,消失的祈祷词,没人再用的语言。
它们缠在一起,摩擦着发出嗡嗡的声音。
一个声音说,「光是借的,借得久了,要还。」
我醒的时候,窗外已经没有月亮了。
只有一块巨大的黑影,把天压得很低。
我妈好像知道什么
后来所有科学机构都乱套了,发的公告一天一个样。有个天文台最后发了条消息,说,「观测失败,模型失效。」
然后所有观测点的仪器屏幕都变成一个符号,一个椭圆,中间一道横线,像一只瞎了的眼。
就像石碑上刻的,“天不再蓝之日”。
那之后,天就慢慢变暗,铁青色,然后是铁锈色,最后是暗灰色。阳光变弱,植物死了一批,又长出些怪叶子。
鸟群乱飞,成群地往大楼的玻璃墙上撞。
人也开始做得梦越来越多。
我们这小城上空刮了阵怪风,不像风,像有很大的东西从天上飞过去。
我被吵醒,听见楼下我妈的咳嗽声停了。
我跑下楼,看见我妈赤着脚站在门口,直勾勾地看着天。
我过去说,「妈?外面冷。」
她跟没听见一样。眼睛里倒映着一道巨大的裂缝,从城上面一直拉到地平线。
我想起了梦里的黑塔。
她忽然开口,声音很飘,「它们下来了。它们终于找到了路。」
我问,「谁?」
她说,「那些没被写进去的神。你总是梦见的那个塔,就是它们埋藏的骨头啊。」
她说话时,眼角流了泪,不是害怕,是觉得这事很荒诞。
我问,「你……怎么会知道?」
她抬起手,在胸前划了一个手势,跟石碑上刻的符号很像。
她慢慢说,「我们家的人,在石碑竖立之前,就已经在守这些东西了。」
我问,「守什么?」
她说,「守它们的‘名字’。只要没有人完整说出它们的名字,它们就被困在塔里,只能通过梦偷一点声音。」
我又问,「那……月亮呢?」
她咳了一声,嘴边有点黑色的血沫,「月亮只是旧时代养它们的壳。壳裂开,它们就会掉下来,找新的地方栖身。」
我问,「新的地方……在地面?」
她摇摇头。
她说,「在语言里。」
遇到一个守碑的老头
几个礼拜后,我们这被划为“阴影带临界区”,但还没撤离,信号就全断了。
我再也分不清现实和梦。那座黑塔好像就立在我家后山。塔身上那些皮下面,我能看见一个个符号正在消失。
梦里那个声音又响了。
它说,「我们饿了。你们忘得太多,丢得太散,只好让我们来替你们收拾。」
我在梦里问它,「你们是什么?」
它说,「我们是你们‘从未说出’的那部分。我们从你们抛弃的神话底下长出来。我们长在缝里,长在删掉的段落里,长在孩子说错话时被捂住的嘴后面。」
它又说,「你们叫我们灾难,但其实我们只是来要回一点东西。」
我醒过来,发现自己站在校门口那块石碑前。
碑上除了“天不再蓝之日”那一行,下面又多了一排字,像从石头里自己长出来的:“当被遗忘者归来……将有一人,以未书之名,将其封回。”
字到最后,石碑裂了道缝。
一个沙哑的声音从背后传来,「你看到了。」
我回头,看见一个很瘦的老人,站在破庙门口。
我问,「你是谁?」
他说,「按旧称呼,我叫‘碑守’。按新编号,我是D-23号精神异常观察对象。」
他给我看了一个泛黄的诊断记录本,上面写着:“长期声称听见石碑说话……对月亮消失有预言性描述……建议隔离观察……”
我问,「是你把这些刻上去的吗?」
他说,「不是我,是它。我们不过是被挑中的墨。」
我问,「它是谁?」
他说,「那座塔。」
我说,「可是它们在梦里…看起来像要毁掉一切。」
他摇头说,「孩子,你误会了。它们做的,只是把你们自己扔掉的东西收回来。你们丢弃了对天空的敬畏,就会有东西来收走它的颜色。你们丢弃了对自己神话,就会有东西来收走你们做梦的权利。」
我问,「那石碑上说的‘那个人’,是我吗?」
碑守笑了很久。
他说,「你觉得呢?你从小做那座塔的梦,听见名字在耳朵后面刮,你以为是谁在叫你?」
我说,「可我什么也不会。」
他说,「正因为你不懂。所以你没被写进去。没被写进去的东西,反而能写别的。」
他给了我一块小石片,是石碑上掉下来的角。
他说,「你把它带上山去。到了塔脚下,闭上眼,什么也不要看,不要听。然后——把你曾经说过却被人阻止的那些话,全说出来。」
我愣住了,「什么?」
他说,「你小时候,想问却不让问的问题,想唱却被说‘难听’的歌,写进日记又划掉的句子……都说出来。那些都是‘未成之名’。你把它们交给塔,塔就会吃饱。」
我问,「那它们就不会再往下掉?」
他说,「不会那么快。灾难不会被阻止,只会被推迟。」
我问,「你守了这么多年,为什么不自己去?」
他说,「因为我早就被写进故事里了。在他们的记录里,‘碑守’是已经被命名的角色。被命名的,就没用了。而你不同,在所有档案里,你只是一个普通女孩。」
上山去跟那个塔说话
我带着石片上山,风很大,有股子腥味。
矿道尽头被石头堵住了,缝里透着黑。
我闭上眼,对自己说,「不要看。」
一闭眼,就听见了风里的低语,都是些我没听过的名字,是那个塔里的东西。
那个声音合成一句话,「你来了。小小的未书之人。」
我说,「我来了。我带来你要的东西。」
胸口的石片开始发热。
那个声音说,「说吧。说你那些没说完的话。我们饿了很久。」
我想起了小时候。
问我爸石壁上的痕迹,他让我别瞎想。问我妈上吊的人为什么不能进普通墓地,她让我别乱说。问老师天不再蓝了怎么办,他笑着说我别说不吉利的话。
这些被卡住的话,我都一句一句说了出来。
我说完了,就又说起日记里写了又划掉的内容:我说我觉得月亮在看着人间偷笑;我说我觉得河底下有条巨鱼,鱼鳞是没写出来的故事;我说我觉得死掉的人都躲在某个字的笔画里。
我都说了。
那个由名字构成的声音一直在吃,周围的耳语声越来越少。
后来,我嗓子干得说不出话了。
我说,「够了。我能给的只有这些。」
过了很久,那个声音才又响起,「你给的,比我们预期的多。我们本来没有形状,是你们不要的词给了我们骨头。既然如此,我们就退回去一段时间。」
我感觉脚下的地沉了一下。周围的嗡嗡声淡了,然后就安静了。
我睁开眼。
矿道还是那样,天还是暗灰色,但亮了点。
远处海上传来一阵轰鸣。
我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。只知道,有东西退回去了。
灾难大概是推迟了
回城里,街上一半都是空的。
我妈在餐馆里睡着了,呼吸平稳。无线电里有断断续续的消息,说有的海域海水开始流动,梦里看不见黑塔了,天文台说月亮的位置多了一圈尘带。
没人能解释。
只有我知道,塔还在,只是暂时睡着了。
带走了我那些没说完的话。
它走之前最后说,「这一次,是你。下一次,还会有别人。」
我坐在我妈身边,看着天边那圈很淡的尘带,想起了石碑上那行字。
那个人不是英雄,只是一个从小到大老被人打断说话的普通人。
后来,天还是没变回纯蓝色。海底下偶尔能看见一点暗影。小孩们不知道月亮烂过的事,管天上的尘带叫“灰环”。
我在城边开了家小书店,不卖畅销书,都是些手抄的故事,小孩画的画,老人记下的梦。
我把它们都收好。
有时候半夜醒了,还能听见很轻的嗡嗡声,像是那个大家伙在梦里翻了个身。
它没有再跟我说话。
我知道,封印不在塔上,也不在石碑上,就在每一个能被完整说出来的句子里,每一个没有被压回去的问题里。
只要还有人愿意把那些“多余的”“奇怪的”话留下来,塔就会继续睡。
直到下一次饿了,再来找另一个说话被打断的孩子。
那时候,灾难会被重新讲一遍。
每一个新故事,都是对旧灾难的反抗。